滚滚圈(作者剪辑版)
◎ 乌青
1
先说一下我的状况吧,有一天,我醒来,发现自己很简单:没有工作,没有女朋友,也没男的朋友,感觉好像我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但是我的年龄实实在在的27岁了,我从床上爬来起,刷牙洗脸,照了照镜子,我的样子很普通,既不帅也不丑(这点你大可以表示怀疑,我不想争执),在人群中只有一种情况才能把我分离出来,就是喊我的名字:乌青,乌青。不过,好像很久没听到有人叫我了。这一天我就在屋子走来走去。
在这个十平米左右的房间里,我来回走了一整天,当然,有时候会在凳子上坐一下,但坐不了多久,因为凳子很硬,坐得我屁股疼(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太瘦了),所以我又会在床上趴一下,一趴就不动了,死了般。直到傍晚时分,肚子咕咕叫。
肚子叫了,该出去吃饭了。我住在一所大学旁边,一般都在学校的食堂里吃饭,但现在已经有点晚了,食堂关门了,我准备在附近吃碗兰州拉面。走到楼下,才发现外面在下雨,妈的,最近天天傍晚下雨,我又没伞,想起屋里还有点饼干,回到房间里,拿出饼干,倒了杯水,开始忧郁地吃起来。
我吃饼干的时候特别忧郁,好像吃的不是饼干,而是奶酪。我吃得迅速,吃着吃着,几乎要哭起来了。多年前,大概七八年前,我也是一个人住在像现在这样的房间里,比现在这个要小,有一天晚上,我像现在这样极度无聊,我买了很多饼干,好几个种类的,一种接着一种的吃,肚子越吃越难受,终于哭起来。我后来告诉别人我吃饼干吃哭了别人都笑,只有一个人表示了理解,他说他有一次因为天气热而热哭了。
这个城市叫武汉,对很多人来说它最有名的一点就是热,但现在我还没有感受到它的热,甚至有点冷,我希望它快点热起来,我不怕热,怕冷。而且这里没有热水器,这种天气洗冷水澡对我而言实在有点勉强。还有我带的睡袋很薄,晚上会感到有点冷。现在是5月中旬,为什么还不热起来呢?我刚刚来到这里没几天。
夜深了,雨也停了。我决定出去走走,解决肚子里依然难以消化的饼干。外面现在非常安静,除了偶尔传来几声狗叫。我走进校园,虽然我来了的这些天每天都进出这个学校,但实际上我对它一点都不熟悉,我从来都是低头匆匆而过,不是去超市就是去食堂,我害怕看见那些大学生,包括男的女的,他们的神情让我感到不知所措,就是那种所谓的青春的朝气吧,我就像在洞穴里呆久了无法接受阳光那样。
现在是深夜,校园里几乎没有行人,所以我感觉比较放松,很快,我发现我好像迷路了。我在一栋楼下停住,开始思索自己的行踪,我是怎么走到这的呢?但是我发现脑子里一点线索都没有,不知道刚才都在想什么。我站了大概五分钟的样子,前面出现一个人影,是个女的,由于环境比较黑,我看不清楚她的样子。我犹豫了一下,决定过去问路。我走到她旁边,说,你好,请问一下,校门怎么走?她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显然她魂不守舍,没注意到我这个人,吓了一跳。我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是人,请问一下校门怎么走?
她看了我一眼(估计也看不清楚我的样子),反问道,哪个校门?这一问我又傻了,靠,我确实不知道我每天走的那个门是哪个校门,我说,我不知道。她说,你不知道,我怎么知道。我说,就是那个周围又很多卖吃的那个校门。她说,每个校门周围都是很多卖吃的。我说,周围还有一个超市,超市楼上是食堂。她这回明白了,然后给我指了个方向,说,你往这边走前面的口子左拐然后右拐然后再右拐然后再左拐然后再右拐然后再左拐就是了,明白了吗?我说,明白了,谢谢。其实我完全不明白,但我又能怎么办呢?总不能要求人家带我去吧。她走进了这栋黑漆漆的大楼,像鬼走进了鬼屋。
我没有走,因为我刚才的问路完全是白问,看来还是得靠自己。我继续站在那思索,但思索也是白思索,刚才那个女孩的声音很好听,我应该跟她多讲几句,如果她没有表示出厌恶情绪的话,我想也没有吧,她都跟我说的那么耐心和详细了,我其实可以尝试让她带我走的。我就想着这些乱七八糟的时候,突然,非常突然啊,天上重重的砸下一个大东西,摔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我赶紧跑过去,一看,我的天啊,是个人,抬头看马上就明白了,这就是传说中的跳楼啊。她趴在地上,双手伸直,双腿扭曲,脸朝下,不过从外形和衣服我已经看出来了,就是刚才我问路的女孩。没想到她最后说话的人是我,我还是很幸运的。但是她现在的样子很恐怖,长发披散。
某些时候,比如这个时候,我的胆子还是很大的,我见过好几次死人,还搬运过呢。我发现有点奇怪,按理说,这么高的楼上跳下来,她的身体受到重击,会导致大规模骨折身体变形和内脏出血,至少头颅会摔破,脑浆涂地。但她没有,她的身体看上去完好无损,简直是奇迹。我感觉她有可能还没死,于是准备动手把她的身体翻过来看看。我的手慢慢地向她的身体伸过去,刚一碰到,我就感觉到了她的体温,然后我开始翻动她,这并不难,她还是比较轻的。我屏住呼吸,做好了看到一张血肉模糊的恐怖的脸的准备。
这时候,我感觉她好像动了一下,我一紧张把手缩了回来,她又回到了脸朝下的状态。接着,我看见她确实动了,她自己翻过了身体坐了起来。她看着我说,你是谁?我依然看不清她的脸,但感觉她的脸是正常的,我真想找个手电照一照。我说,我就是刚才问你路的人,你还记得吗?我怀疑她已经失忆了。她说,哦,你也死了?我说,拜托你别说那么恐怖好不好,我好端端的怎么死了。她的神情显然有点恍惚,又问,这是哪?我说,我哪知道啊,刚才我还问你路呢?她使劲甩了甩头,说,我没死吗?我说,应该没死吧。她说,怎么可能?我这么高跳下来没死?我说,今年我不仅见到了跳楼,还见到了奇迹。她说,你在这干嘛?我说,我,我,我。她说,你是不是就是来看我跳楼的?我说,我怎么会知道你要跳楼啊,我又不认识你。她说,那你大半夜的在这里干嘛?你是不是人啊?我说,我只是想再问问你,那个校门怎么走。她说,你等我跳楼就是为了问路?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说,我还是不知道怎么走。她说,那你刚才说你明白了。我说,我怕打搅你跳楼。她说,那你还是知道我要跳楼咯。我说,我怎么会知道,操,我就这么一说。她站起来,说,好吧,我带你去。我说,那太好了,多谢。不过我能不能问一下,你是不是人啊?她说,我还想问你是不是人呢?我说,我当然是人了,我怎么不是人。她说,那我怎么不是人了?我说,你刚才是人,现在就不一定了。她说,那你刚才就不一定是人。我说,好吧好吧,不管是不是,麻烦你带我出去。
我们很快走到了有路灯的地方,我开始打量这个女孩,首先她长的很漂亮,其次一点都看不出刚刚跳过楼,以至于我怀疑刚才跳楼的事情是不是幻觉。我说,你没事吧。她说,有什么事啊?我说,你真的没事?要不要去医院?她说,说了没事就没事。我说,你是不是人?她停住了,说,你有完没完?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学校很少见到你这么漂亮的人。她说,你别油嘴滑舌了。我说,你怎么会没事呢?她说,那你希望我有什么事?死了?我说,我当然不希望你死,你死了,我不定就成了嫌疑犯呢。她说,那你还问这问那的。我说,这事搁谁碰到了都会好奇啊。那你为什么要跳楼呢?她说,你问那么多干嘛?再问你自己走。我说,好吧,不问了。
2
有一天,我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而周围的环境异常安静,我必须要想一想才明白自己的情况,我发现我的情况很简单。这个小屋子非常安静而且非常安全,相信没有任何事物会来打搅我的安静和安全。我起床,走到桌子旁,倒了一杯水,正要喝。门发出砰砰的声音,我确定了一下,是有人在敲我的门,这真是一件令人充满好奇的事情,谁会来敲我的门呢?我并没有马上去开门,脑子里迅速做出种种猜想,首先我想的自然是房东,但这个可能性极小,他没有理由来找我,房租已经付了,包含了水电费宽带费,屋子里也一切正常。昨晚跳楼没死的那个女的?那更不可能,首先她不知道我的住处,虽然昨晚我已经努力邀请她了,那种邀请意图太明确,她拒绝了,其次我想不出她找我干嘛,难道邀请我再去看一次她的跳楼?坦率说,那个事情我现在也没搞清楚是真实的还是我的梦,如果她接受了我的邀请,早上起来,她躺在我的床上那我就承认是真实的。
门继续敲着,节奏加快,我站在离门不到一米的位置,门被敲的一震一震,声音在我的听觉里越来越大,已经影响了我继续的思索,否则我会把我认识和不认识的能想到的每个人都想一遍,每个人如果真的来找我,他们的来由又都是不同的,某个男的会不会莫名其妙的送来一袋金币,某个漂亮的姑娘会不会莫名其妙的爱上我。终于,我开了门,答案揭晓了。
我操,门口站着的压根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垃圾一样的怪物,它的脖子上长着至少100个葡萄大小水晶状透明的小球,每个小球里都是一张一摸一样的脸,它开始说话,你好,我只是来告诉你一下,地球已经被我们占领了,你不必恐慌,你依然很安全,你可以继续睡觉。说完,转身就走,它的腿至少有1000条,都很短,再它身体下面快速蠕动,走的起来还挺快,但这么短的腿,怎么下楼呢,我有点好奇,所以注视它接近楼梯,它在楼梯口停住,回头看我,100张脸上的100张嘴巴异口同声地说,你他妈的开门也太慢了。说完,身体某处伸出两只昆虫般的翅膀,蜜蜂一样嗡嗡地飞走了。我心想,有翅膀你丫还长那么多腿干嘛?
一切都很平静,这个世界什么都没发生,仅仅是地球被外星生物占领了,这关我P事啊。这个汉语说的相当标准(居然还会说他妈的)的外星人既没给我带来金子也没带来姑娘,连恐惧都给我没有带来。他来了跟没来一个样。
关上门,又躺到床上,用被子蒙住头,我发出呜呜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我坐起来,找不到眼镜了,刚刚我躺下的时候,把眼镜放哪了我忘了,这只是三十秒前的事,我居然想不起来了,我在床上翻找,没有,床头柜上也没有,桌子上也没有,这是什么事啊?我开始在整个屋子里疯狂地寻找,找眼镜确实太麻烦了,因为没戴眼镜我本身就看不清楚,我心想掘地三尺也要把你找到,如果有把锄头我马上就开始掘地,当然,我住的是二楼,我会把地板挖个洞,看到一楼的房间里,也许一男一女正在做爱,即使那样,我也看不清楚。我发现了角落有个塑料袋,里面是我前天买的一种巧克力饼干,我吃了一片,觉得不好吃,现在我又拿起一片吃,觉得更难吃了。我正准备把它扔到垃圾捅里,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扔掉有点可惜,我不喜欢也许别人喜欢,为什么不把它送给别人呢?可是送给谁呢?能不能随便找个女的送呢?必尽这个饼干是好的,而且还不便宜呢。
但是现在的事情是找到眼镜,不过我马上找到了,妈的,就在床上。好了,现在我要出去送饼干了。我拎着饼干出门了。
天气不错,傍晚的微风吹拂,我觉得我的心情既不愉悦也不忧伤,我没有什么好高兴也没什么好郁闷的。我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垂头走在那些学生的中间,看到两旁的树,会产生一种想要去拥抱它的欲望。当我抬起头的时候,迅速观察周围的女生,转了几圈后,我选定了一个跟踪目标,我跟在她的后面,很自然,这么多人走来走去,跟踪事情显得隐晦,我非常喜欢看漂亮女生的背影,她走路的样子臻于完美,真希望可以一直这样跟踪下去,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跟踪,她终于要走到女生宿舍里去了。就在即将进入宿舍楼的时候,她停住了,她回头看我,我愣住了,她向我走过来,说,你干吗跟踪我?她正面的样子不如背影迷人,但如果她愿意的话,我肯定也愿意跟她拥抱,至少感觉会比跟一棵脏兮兮的树拥抱来得舒服,树没有乳房。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在跟踪你?她说,你不承认?我说,我当然不承认,路上这么多人走,凭什么说我跟踪你?她说,你刚才在我后面说一句话,你以为我没听到吗。我说,我说了什么?我怎么不知道。她说,你说天下没有不散的跟踪。我说,我说了吗?我以为这句话是在肚子里想的呢。她说,你想干嘛?我说,我,我想送一样东西给你。她说,什么东西?我把手里的饼干递给她,说,这袋饼干,巧克力的。她笑起来,说,你干嘛要好端端的送饼干给我?我说,因为这个饼干不好吃。我又说,别别误会,只是我觉得不好吃,其实挺好吃的,你可以试试,如果你也觉得不好吃可以不要。她没有理我,转身走进宿舍楼。
能有什么办法呢,这年头送袋饼干给别人也这么难啊。我听到一个笑声,转身看了看四周,发现是一条土狗。它对我说,别送给人了,没人会要的,送给我吧。我说,饼干你吃吗?它说,我确实是不喜欢吃饼干,尤其是巧克力的,但没人要还不如送给我呢。我说,那好吧。就把饼干给了那只狗,它说,下次我送你一块骨头。
4
有一天,我从外面回到家里,打开门,心一下子凉了。我看到我的房间里空空如也只有四面墙壁,从那一刻起我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小时候,我跟我父亲吵起来,他很生气,从厨房里拿起菜刀,对我说,YES
or NO?我泪流满面,咬着牙,说,NO。我看着父亲握着菜刀的手举在空中剧烈地颤抖,从那以后,我一紧张,我的手也会剧烈地颤抖。所以看到《拯救大兵瑞恩》里汤姆汉克斯的手颤抖的时候,我特别难忘。父亲说,你给我滚。我说,滚就滚。父亲说,再也不要回来。我说,我再也不回来了。父亲说,把衣服裤子全给我脱下来,你一无所有。比起父亲来,这位小偷还没那么绝,至少没有偷走我身上的衣服。我还可以出去。于是我来到街上,就像我还没有回家,还不知道家里发生的一切。我开始奔跑,不停地跑,两旁的树木纷纷后退,我抬头往向蓝天,天空真空旷啊,一朵云比另一朵云更远。渐渐地,我感到头皮有点发麻,似乎有什么东西从头上长出来,一摸,果然头顶两侧长出了两根火柴棍大小的东西,好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捏重了会疼,有点弹性。我失去了也许我从来就没有拥有过的一切,却多出了两根火柴棍触角,它有什么用呢?又不能用来点烟。
进到一个公共卫生间,我对着镜子仔细观察了一下我的触角,它确实像火柴棍,再也没有别的了。不过,当我停止奔跑心跳慢慢恢复平静的时候,我看见它慢慢的缩了回去,摸摸头顶,也毫无痕迹,我试图用意识让它再伸出来,像便秘一样使劲憋红了脸,它确实也伸出了那么一点点,然而一放松又缩回去了。算了,不管了,只要以后洗头或理发的时候它不长出来,应该也没什么影响。
这时候遇到了一个女生,她就是我曾跟踪她送她巧克力饼干她不要的那个女生,她开心的走着,手里拿的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一袋巧克力饼干,准确的说,那就是我的巧克力饼干,我只所以这么准确是因为,我觉得那就是。我栏住了她,她看了一下我,说,你干嘛?我说,你这袋巧克力饼干是哪来的?她说,管你什么事。我说,是我的。她说,什么你的,是别人送我的。我说,有没有搞错啊,我送你,你不要的嘛,你不记得了?她说,你瞎说,你什么时候送我了?我都不认识你。我说,就前天,我跟踪你,然后送你这个,你没要。她说,前天我一天没在学校里。我说,不可能,那你说,谁送你的。她说,不管你的事。我说,我一定要知道,不然我就。她说,你就怎么样?强奸我吗?我说,难怪你不说,你已经知道后果那么美好了。她恶狠狠的拧了我的胳膊,我说,你这人怎么莫名其妙的,干吗拧我,我跟你很熟吗?她说,谁莫名其妙,是你拦住我的,老大。我说,我就是想知道你的饼干哪来的。她说,你这还不够莫名其妙吗?要不要喊人来评理?我说,好吧,我说不过你,你也拧了我了,我也没还手。她说,你敢?我说,好吧,我不敢,你也拧了我了,我也没还手。她说,你敢?我说,操,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她说,你还有什么话?我没时间搭理你。我说,你以为我时间很多吗?她说,我看你就是时间太多了,经常看你晃来晃去的。我说,好吧,我是很多,但你没时间啊。她说,所以我不陪你胡说八道了。我说,所以你赶紧告诉我饼干哪来的,你就可以忙你的去了。她说,我不告诉你我也可以走。我说,你他妈的都拧了我了,我都没还手。她说,你敢?我说,你能不能讲理点。她说,谁不讲理了,是你不讲理。我说,一直在跟你讲理。她说,你莫名其妙拦住我你还有什么理?我说,我哪里是莫名其妙的拦住你,我拦住你的是有问题问你。她说,你这人就是有问题。我说,你才有问题呢。她说,你自己刚说自己有问题的吗?我说,你讲不讲理啊你?她说,我懒得理你了。欲走。我说,等等,你真的经常看到晃来晃去的?她没理我,走了。
莫名其妙被她拧了一下,也没问到饼干的来历,这太不公平了。
她向食堂走去,这个时间应该是去吃饭,我才感觉到自己也很饿了,但现在身无分文,我应该把饼干要回来当晚餐,虽然难吃点,或者她至少得请我吃顿饭吧。于是我也向食堂走去。
食堂的人已经不很多了,我看见她拿着托盘,点了几个菜,走到一张桌子前坐下。我走过去走在她对面坐下。她说,你怎么又跟来了,有完没完还?我说,又是什么意思,你承认我跟踪过你咯,你刚不是说不认识我吗?她说,你再不走,我喊人了。我说,我又怎么你,你喊什么?她说,你骚扰我。这句话有点伤害我,我说,我真的骚扰你了吗?她说,这很显然嘛,不是骚扰是什么?我说,可是我的饼干。她说,什么叫你的饼干,这饼干上有你大名吗?她的声音有点大,引起了旁边几个男生的注意。我说,你能不能小声点,我可不想被误会。她说,你到底想怎么样?是不是要跟你上床才肯罢休?这时候旁边的男生中有一个比较高大头发很长的坐了过来,说,需不需要帮忙?我说,谢谢,不需要。他说,操,我又没问你。小姐他是不是骚扰你。我说,操,我又不是跟你说。那男的马上站起来,另外的三个男的也立刻站起来,四个人把我围住。我感到事情已经糟糕了,心里有点恐惧。我说,好吧,我走。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一个乞丐。我也站起来,但是那个长头发马上把手放到我的肩膀上又把我按回去,我心想,这是一件多么糟糕而庸俗的事情啊,而我扮演恰恰是这件糟糕而庸俗的事情中最糟糕而庸俗的角色。他像电影里的流氓一样摆出一副装B的德行,说,你这样就想走?我没有说话,心里列出了两个方案:1、好汉不吃眼前亏,认了,委屈求容,也许他们骂几下就算了。2、先下手为强,突然爆发的攻击对方,然后乘其不备,迅速逃跑。怪我想了久了点,还没来得及作出选择,那家伙就已经一巴掌打在了我的左脸,顿时火辣辣的疼。心跳顿时跳得厉害。除了我爸还没谁打过我巴掌呢。然后他说,我们到外面谈谈吧。几个人拽着我就往楼梯口走。毫无疑问,我将在某个角落被海扁一顿,我边走边把眼镜摘下来放到裤子口袋里,免得到时候眼镜不知道飞哪去了,又是一笔损失啊。我回头看了一下那个女生,她脸上的表情难以琢磨,可能也有点害怕。他们把我推拉到楼梯口拐了个弯,进入一个男厕所。我这才知道这里有个男厕所,之前好几次我在食堂想找厕所只发现了女厕所,靠,原来在这里。接下来的情况很简单,我缩在角落用膝盖和手臂护挡他们的一顿拳打脚踢。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他们好像没使什么劲,我的痛感并不严重,但看他们的神情确是十分卖力的。完了,他们骂骂咧咧的走了。我站起来,拍拍了衣服,相当轻松,像玩了一场游戏。我走到水龙头前,洗了洗手,洗了把脸,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嘴角和鼻子有点血迹,头发凌乱,在头发中两根火柴棍又长出来了,那样子好像还有点酷。我隐约感到自己获得了一种神奇的力量和信心。我对着镜子里做了一个李小龙式的用大拇指擦鼻子的动作,然后撒了一泡尿。洗了洗手,做了一个深呼吸,莫名其妙地叫了一句:WOW。
食堂里已经几乎没人了,大厅显得十分空旷,整齐的桌子凳子,静止的。那几个家伙此刻正围着那个女的,如果说他们刚刚对我的行为勉强算英雄就美的话,那么现在角色发现了转换,他们分明在骚扰那个女的,那动作让我怀疑他们是不是在演电视剧。我大喊了一声:停。他们一下全都回头看我,表情有点惊讶,长头发说话了,操,你以为你是导演啊?我说,你们充其量就是群众演员,连名字都没有的那种。长头发说,你是不是还嫌当替身当得不够啊,这回让你尝尝我们的狠。我说,你们是不是搞乐队的?长头发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这造型,是不是玩死亡的?长头发说,你丫还有点眼光啊,不过我们正准备转工噪。我说,你们乐队叫什么?他说,叫生不如死。我说,好,那今天就叫你们生不如死。长头发将手一挥,弟兄们,为了摇滚,冲啊,嘟嘟哒嘟嘟。我一动不动,说,跑那么快干嘛,你们以为你们是音速青年啊。一个手臂有纹身的胖家伙最先跑到我面前。我说,你是不是主音吉他?他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你跑场最快嘛,你这纹身没纹好,退色了。他说,你懂个P,我这是日式的。我说,日式哪有萨摩亚式牛啊。他说,少废话,动手吧。我说,你先。他说,为什么要我先。我说,你先显得我比较酷嘛。他说,我操,警察来了,我先动手我吃亏啊。我说,既然这么说,那就我先吧。他说,来吧。我说,还是你先吧,我觉得还是你先比较好。他说,你先。我说,你先。他说,你先你先。我说,你先你先。他说,操,那不来了。我说,好吧好吧,我先就我先。我把我拳头慢慢放到身后,然后击了出去,击中他的嘴巴,他的脸立刻变形,所有的牙齿向四处飞出,而身体也随即腾空,迅速向我的前方飞去,飞出食堂,飞出阳台,飞向远方,消失在地平线深处。长头发大喊一声,啊,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天马流行拳。我说,错,这叫乌青拳。他说,啊,好像有这个短片。我说,现在该你了,妈的,刚才居然打我左脸。说着,我用手背一扇他的右脸。他侧身飞起,我再使出一记威力更大的乌青拳,他立刻像发射的火箭一般向前射去,然后我biu的一下闪到阳台,在他即将飞出阳台的瞬间又抓住了他的腿,甩回了食堂。他至少也是临床死亡了。剩下的两个也纷纷获得了生不如死的资格。我站在那里,又莫名其妙的说了一句:一曲肝肠断,天涯何处觅知音。
好酷啊,那个女孩拍手叫起来,如果戴付墨镜就更酷了。我说,恩,但我没钱买。她说,我送你我送你。我说,我还没吃饭呢,要不你请我吃饭吧。她说,好啊,走吧我们到外面吃去。我说,等等。我走到那几个家伙那一一掏了他们的口袋,总共大概有两三百块钱。我对生不如死们说,下次多带点。然后和那个女孩一起走出食堂。女孩边走边说,你头上的角好酷啊,像那个地狱男爵。我说,不是吧,地狱男爵那个好粗啊,我这个这么细,而且人家是一个,我两。她说,细点没关系,威力大就好。我说,这话有点汗。她说,那几个群众演员,连名字都没有,我有没有啊?我说,有有有,你有。她说,那我叫什么?我说,R2。她说,这不是星球大战里的机器人吗。我说,不是,你是我遇到的第二个女孩,所以叫R2。她说,那R1是谁?我说,R1比你漂亮。她说,哼,导演都是色狼。我说,不过,你的背影比她好看。我下一部片子就叫《背影》。她说,是拍朱自清那个散文吗?我说,当然不是,你来演吧。她说,那是什么样的片子。我说,鬼片。她说,哼,人家才不要演鬼呢。我说,没让你演鬼,你演鬼的背影,替身。她说,哼,我不请你吃饭了。我说,靠,那我不是白英雄救美了。她说,你救什么救啊,他们又没怎么我。我说,我看他们围着你调戏你的嘛。她说,谁告诉你围着就是调戏的。我说,那他们围着你干嘛。她说,他们说想找我做他们乐队的主唱。我说,我还看到那长头发的手在你的胸部这里摆弄来着。她说,你看得还真仔细,那是他在跟我讨论气息。我说,不是吧,你一小姑娘家去唱死亡金属?她说,我去了肯定就改变风格了呗,我们准备搞工业舞曲。现在女的搞摇滚容易红,还能演电影,还能出书。比如那个田原。我说,人演的是同性恋,还不如演鬼影呢。她说,哼,那是艺术片,你的鬼片是商业片,不是一个档次的。我说,艺术片得有床戏,你干吗?她说,那得看跟谁合作了。我说,我自编自导自演行不行啊?她说,你,那得看片酬。
6
不知不觉来到了一栋楼底下,夜已深。在阶梯上坐了下来。我的手里拿着一瓶牛奶。此刻,我坐在这里喝着牛奶,我会把这瓶牛奶喝光——真希望它永远喝不完,我会坐到天亮——真希望天永远不亮。就这样过完一辈子,就完了,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突然,天上重重的砸下一个大东西,吓了我一跳,我走过一看,是个人,再一看,不是别人,又是那个R1,就是上次跳楼没跳死的女孩。我想这次她总该死了吧,但她很快又动了动,然后又站起来了。她看到我说,你怎么又在这儿啊?我说,我刚好路过,在这坐一会。她说,你又迷路了?我说,这次不是迷路。她说,那是专门来看我跳楼的?我说,鬼才知道你要跳楼。她说,那你的意思是说你是鬼?我说,我懒得跟你绕。她说,你在这到底干嘛?我说,我在这喝奶,你要不要?说这把牛奶递给她,她接过去,喝了一口,然后用手背擦了擦嘴角,说,谢谢。我说,我没地儿去,能不能去你那?她说,你上次让我去你那,这次改去我那了?不成。我说,真的,我真的没地方去了,再说,你都喝了我的奶了。她说,不是吧,就喝口奶。我说,我爱上你了。她顿时愣住了。我说,不过我不知道怎么谈恋爱。她看着我说,好吧,去我那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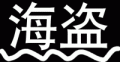 ┩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