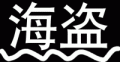小气鬼
◎ 吉木狼格
打狗运动过去后,人们又开始养狗了,曾经一度单调得只有人的县城,又出现了人狗共处的局面。这些狗大多来自乡下,即本地土狗,只有崔四哥养了一条藏獒。关于它的来历,崔四哥始终不对我讲,我一问,他就做出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真让人难受。
我有大半年的时间没到宣传队来找崔四哥玩了,我在生他的气,因为他不让我喝酒。他总爱说你一个小娃儿喝什么酒。我已经上初中了,就算不是大人,也不至于像他说的小娃儿!开始我以为他舍不得给我喝,是个吝啬鬼,一天我从家里偷了一瓶酒来,他一把夺过去自斟自饮,就是不让我喝。看来他不是因为吝啬,他的确不像个吝啬鬼,但他凭什么不准我喝自己的酒?我一怒之下冲出宣传队的大门,发誓不再理他。
我生了崔四哥半年的气,本打算继续生下去,但半年后气就消了,不仅气消了,我还常常有点儿想他。不管怎么说,崔四哥显得与众不同,在这座县城,他看得起的人没几个,同样,在这座县城,像他这样的人也没几个,甚至独一无二。你看,半年不见,与众不同的他就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条藏獒。
我别别扭扭地来到崔四哥寝室的门前,见屋里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我听见崔四哥大声喊:
“趴下,不许起来。”
崔四哥在屋里向我招手,我进去后,被地上那团黑乎乎的东西弄得有些紧张,我绕开它坐到沙发上,而它的头随着我转动,一直在看我。这是什么东西?我想,这是狗吗?狗哪里有这么大、这么威风?
当它从地上站起来,更让我吃惊,它不仅高大,而且肥壮。
“不要怕,”崔四哥说,“它来向你打个招呼。”
它走到我跟前,闻了闻我身上的气息,然后沉默地望着我。
我想摸它一下,但是不敢,我坐着一动不动,甚至不敢与它对视,只好看它一眼,再看崔四哥一眼。等它转身走开,重新趴在地上,我紧张的心情才松弛了下来。
我和崔四哥半年不见,本该感到尴尬,可是有它的存在,我们来不及尴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仿佛它成了我们之间和好的桥梁。
“它是狗吗?”我问。
“不是,”崔四哥说,“它是藏獒。”
我听人说过藏獒是世界上最大的狗。崔四哥说藏獒不是狗,在这个愉快的气氛下,我很乐意接受。狗是狗,藏獒是藏獒,狗不是藏獒,藏獒不是狗。
它巨大的脑袋和皱巴巴的脸,总让我想起狮子,虽然狮子是黄色,它是黑色。
崔四哥从柜子里拿了一瓶酒出来,他又要喝酒了,看他喝酒让你觉得,对他来说,酒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他拿了两个(而不是一个)杯子放在茶几上,倒上酒后,他端起其中的一个对我说:
“来,干了。”
半年前他死活不让我喝酒,我们为此翻了脸,半年后他主动给我倒上酒,这说明他不再当我是小娃儿。
我学他的样子一口干了,把杯子放回茶几上,他笑眯眯地看着我,没有说话。我倒上酒端起一杯对他说:
“来,干了。”
我们又干了。
“你的酒量怎么样?”他问。
“不知道。”我说。
我想喝酒,也偷偷喝过几次(几口),但像今天这样正式地和一个人喝酒,还是第一次。我能喝多少、酒量有多大,自然不知道。
干了两杯后,我们不再干杯,而是想喝的时候,各自端起酒杯喝一口。
“它不是狗吗?”我指的是藏獒。
我发现我喝了酒之后想说话,想弄一些问题来解决。
“它是万兽之尊。”崔四哥说。
他把它说得比豹子老虎还要厉害,狮子也不过是“百兽之王”,而它是“万兽之尊”!那么它当然不怕凶猛的野兽,相反,它们应该怕它。我知道豹子是狗的天敌,狗一看见豹就浑身瘫软,任由其撕咬并吃掉。藏獒不是狗,它不怕豹子。该不会豹子看见它就要瘫软吧?
“它一吼,”崔四哥说,“方圆百里就平安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问。
“就是说,”崔四哥喝了一口酒,“听见它的吼声,所有的野兽都会远远避开。”
“你是从哪里弄来的?”我羡慕地问。
“半年前我出了趟远门。”崔四哥说。
“有多远?”我问。
“很远,”崔四哥说,“也很高,纯种藏獒只有在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的高原才有。”
“你是说你去了一趟藏区?”我问,“你是从那里把它带回来的?”
崔四哥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干了半杯酒,手指在空中打个响,吆喝趴在地上的藏獒到他跟前来。他一手摸着藏獒的头,一手给空了的杯子斟酒。我对他的藏獒是从哪里弄来的充满兴趣,问了几次,他总是笑眯眯地喝酒,或者转移话题。我只好在心里猜想他真的是从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的藏区千里迢迢弄回来的。我也有点怀疑他并没有去那么远,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得到了这只藏獒。
他和它那种亲密无间的情形,好像相处了很久,其实只有半年,也许那时它还没有完全长大,喂养了半年才长成现在这么大。
“它是纯种藏獒吗?”我问。
“百分之百的纯种。”崔四哥说。
在酒精的作用下,崔四哥的话使我开怀大笑。我喜欢他吹牛,喜欢他吹的牛。
我们正在喝酒,田姐敲门进来了,那只藏獒跑过去摇头摆尾,显得极为亲热。田姐是崔四哥的女朋友,我认识她——我是说不管她是不是崔四哥的女朋友,我都认识她,我在街上和大礼堂的舞台见过她——她也是宣传队的,在众多美女中,我觉得她最漂亮。
田姐一进来,崔四哥就暗示我该走了,我从沙发上站起来,头有些晕,身体轻飘飘的。走到门口,崔四哥对我眨了眨眼睛,然后关上了门。
我保持平稳,摇摇晃晃地走出宣传队。
第二天,我又来找崔四哥玩,门开着,我刚一进去,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朝我猛扑过来,崔四哥一声喝止,那团东西仿佛定格在空中,随后滑到地上,它和我的距离只差没有碰上。不是崔四哥喝止,我早被他的宝贝藏獒扑倒了。
“你干什么?”崔四哥指着它说,“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知道吗?”
崔四哥迷雾着眼,满嘴酒气,他又喝醉了。
“你可以谁都不认,”他说,“但是你必须认他……听见了吗?你们两个出去转一圈,正式成为朋友……去……”
崔四哥说的是人话,而不是对着它汪汪叫,我听懂了,它不是人,能听懂吗?但它真的和我一起出了门。我不敢带它上街去,我是它的朋友,但别人不是,它发起威来我无法阻止。我带着它在没人的地方瞎转,它似乎对周围的环境不感兴趣,我到哪儿它到哪儿,亦步亦趋,紧紧跟随。不过,与其说它听我的话,不如说它在完成崔四哥交给它的任务。
转完回来,房间里多了两个人,一个喝醉了,正在和崔四哥争论,一个没醉,坐在一边听他们争论。我也坐下来听,可听了半天还是听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看来他们说的是只有他们两个才明白的话——酒话。说到激动处,那个人站起来指着崔四哥大声分辨。嗖的一声,我眼睛一花,那个人已被崔四哥的藏獒扑倒在地。它没有俯下去咬他,而是傲慢地昂着头,在它庞大的身躯下,他根本动不了。
崔四哥笑着把他的藏獒叫开。
“你的狗搞偷袭,”那个人站起来说,“这次不算,再来一次。”
“算了吧,”崔四哥说,“十个你加起来也摔不过它。”
“不行,”那个人说,“非摔不可。”
崔四哥叫另一个没喝醉的赶紧把他弄走,否则要出事的。到了外面,他还在不服气,嚷着要和崔四哥的藏獒比个高低。
“酒醉的人真是胆大包天。”我说。
“这是个傻瓜,”崔四哥说,“不知道它的厉害……上次有个人喝醉了,听说我养了一条藏獒,想来会会,他歪歪倒倒地串进来,一见它就吓醒了,它还没有扑过去,这家伙转身就跑……而且……一溜烟跑得飞快……”
我哈哈大笑,给自己倒杯酒,端起一饮而尽。趁崔四哥高兴,我又连干了两杯。
“小县城的人真是无聊,”崔四哥说,“不就是一条藏獒吗……大惊小怪的……”
他说是这样说,但我听得出,他对自己的藏獒十分满意。
宣传队的人没什么事可干,女的忙着谈恋爱,男的以喝酒消磨时光。他们个个是酒鬼,整天泡在酒里,不醉不休。所以宣传队的女的都不在本单位找对象,惟一的一对恋人就是田姐和崔四哥了。但田姐的父母坚决反对。我想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崔四哥,他们只看到了崔四哥喝酒的一面,却不了解崔四哥与众不同的地方,比如,他看不起整个县城的人。
要让田姐的父母同意,崔四哥就得改变形象——每周喝一次酒,最多不得超过两次,并且只能在自己的寝室喝——这是田姐对崔四哥的要求。
让一个酒鬼每周有五天不能喝酒,这不是要他的命吗?
田姐的父母对她管得很严,晚上九点以前必须回家,她只有在白天上班的时间和崔四哥在一起。她一走,崔四哥常常溜出去喝酒,被她发现了几次,每次她都说你再喝我们就吹,每次崔四哥都保证不喝了。
崔四哥很喜欢田姐,他天不怕地不怕,只怕田姐,怕田姐发现他喝酒,但田姐偏偏会出现在他喝酒的地方。这要归功于他养的那只藏獒,它好像存心收拾崔四哥,总是出卖他,准确无误地把田姐带去,田姐一到,它转身就往回跑。
周末的晚上,我来到崔四哥的寝室,他正在骂他的藏獒,不用说他喝醉了,他坐在沙发上,藏獒站在他跟前,像一个做错了事的人,看来它又把崔四哥给出卖了。
崔四哥一边骂一边哭,显得既伤心又愤慨。
“你个吃里爬外的东西,”崔四哥说,“我辛辛苦苦养你……你却出卖我……咹……你简直不是人……”
我不知该怎么办,要不要安慰崔四哥?看他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我也替他难过;再看他的藏獒,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下次它肯定还要出卖崔四哥),我又觉得好笑。
但最好笑的是,崔四哥给他的藏獒取了个古怪的名字——小气鬼。
威猛高大的万兽之尊叫小气鬼,亏他想得出来。它和它的名字,这两样极不相称的东西联在一起,够幽默的,我以为崔四哥追求的正是这种滑稽的效果。
“你看嘛,”崔四哥说,“它真是个小气鬼。”
我看不出来。直到有一天,不知什么原因,崔四哥把它惹气了,我进去的时候,崔四哥端了一个饭钵放在它跟前,只听砰的一声,它用前爪把饭钵打翻了,并把头扭到一边,坚决不吃。
崔四哥对着我笑了笑,拿扫帚扫干净地上的狗食,重新装了一钵。
“来,乖——”崔四哥说,“吃吧,啊——”
这次它没有把饭钵打翻,但把头扭得更远。
崔四哥又是搂又是抱,什么“对不起”,什么“你真乖”,各种肉麻的话弄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哄了半天,它才皱着脸,委委屈屈地吃起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