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
◎ 小平
去年三月的一天,二马给我打电话,说小张和小静要在四月份结婚。
之后小张打电话给我,说他和小静要来南京买东西,所以把请柬就直接给我带来了。
婚礼定在周日晚上。二马让我周五晚上就过去,好聚聚。我因为有事情走不开,等到周日当天的上午,才乘火车去常州。
听到小张和小静结婚而不吃惊的大概没有几个。在高中的时候,小张就喜欢小静,甚至在毕业前夕,小张也因为小静不理他而在小静的宿舍楼底下痛苦流涕。自始至终,小静没有给过小张一点机会。毕业那次小张的痛哭和小静的静,让我们觉得就像绝响。大学期间,小张有一次去苏州玩,约了一帮同学,就是没凑齐小静。两个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往来。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然而,正是他们,结婚在即。
大学毕业后,小张分配在常州的一家银行上班;小静分配在常州的一所大专院校任教。据说,某一天,小张心血来潮,给小静发了条短消息,问她有没有交男朋友,就这么直接。一个疑点是,小静的手机号码是怎么冒出来的,这可是真正的蛛丝马迹。总之,小张和小静开始有了联系,直到现在他们结婚。
这个说法类似版本的提供者有三个:一个是二马,他和小张关系一向不错,特别是大学毕业后,两人交往更是密切。按照二马的说法,小张突然觉得对目前的生活有些厌倦,疲于寻欢做爱,想要找一个正经过日子的女人。小静是其中的一个,但肯定不是唯一的一个。小张给小静发消息在他有这个念头这之前还是之后,已不可知,并不重要。
还有两个是小张和小静,地点是在南京大排挡,在场人物为:小张,小静和我。他们的叙述,两人的接触同样也始于手机短消息。小张说,有一天,小静给我发了一条短消息,问我还有女朋友了,我说没有,正等好着你呢。此话遭到了小静的反驳,她说也不知道是谁无聊,先给她发短消息的。虽然还是笑着,但已然有点生气。于是我们在饭桌上奋力游向其他的话题。我有些心不在焉,心里一直在想着“无聊”这个词。
关于在最初的短消息之后,小张和小静的联系,必定和天下所有的男女一样,在曲折中前进着,其间,既有所谓的爱,也避免不了污秽。他们的结婚,也许并不像我所想的那么突然,因为其突然而觉得其简单,这就更加的谬误了。
下火车后我先买了当晚回南京的车票,票紧张,只买到九点半的站票。酒席在6点开始,三个小时我觉得差不多够了。入席后,我才知道原来和我坐同一车次来的,又买了相同的站票回去的,还有三个人,他们都是小张大学的同学,其中有一个还是我溧阳老乡。他们和我们几个坐了一桌。小张并没有请更多的同学,高中女同学更是一个也没有。我想不到小静也许竟会是一个孤僻的人。
到八点半的时候,我们坐不住了,新郎敬酒还遥遥无期。我们原来是打算最好等新郎敬酒后我们再离席,这样一来,恐怕就赶不上火车了。我的溧阳老乡就过去跟新郎耳语,不出我们所料,小张不同意我们这么早走,说赶不上火车就赶不上好了,他已经让人把我们的宾馆都开好了。但明天是周一,我们不可能在常州住一晚上。这个时候狄皮想到他认识一个女孩在常州火车站工作。那个女孩说可以帮我们改签,但因为我们买的是站票,所以,她不可能帮我们换票种,依然还只能是站票。这已经很好了。这样一来,我们就一直呆到了酒席的结束,只是没有闹洞房而已。
上车后,我们四个占了两节车厢之间的一个过道。晚上喝了好多酒,人真是很困,干脆就坐在车厢地板上。不停的看时间,想到南京还有多少时间,每减少半个小时,我们都不由得振奋。睡意朦胧间,有一个人也来到了我们的这个过道。说是一个人,只因为我乍一看看不出来是个男的还是女的,不由的清醒了好多,仔细拿眼扫描,还是辨别不出这个人的性别,我的兴趣越发的浓了。
我不知道这个人什么时候上的车,也不知道这个人具体什么时间突然在我眼前冒出来。出现后,这个人就一直没走到别处去,到镇江才下车走了。这个人在的时候,我一直忍不住去看,又怕和这个人的目光对着了,我想这个人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这真是很难看出来。我偷偷看这个人的胸部,小腹,甚至裆部,但是无论哪里也不能帮我提供证明。总之,我一会觉得应该是个男的,一会又推翻,觉得其实是个女的。如果是个男的,那他就很女性化,如果是个女的,那她就很男性化。如果他是男的,那就没什么;如果她是女的,那就很奇怪了。我想如果她是个女的,我,或者是换一个别的男人,会愿意跟她结婚吗?
我被我这个想法吓了一跳,害怕起来,不再敢看这个人,可又忍不住去看,真有点百爪挠心的感觉。有一段时间,这个人靠着我对面的墙站着,个子瘦而高;有一段时间,这个人撑圆两腿坐在我对面,两腿细而长。我一会发现他是个男的,心里很高兴;一会发现她是个女的,心里又很慌乱,这个慌乱介于想看又不敢看之间。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我产生幻觉,自己像一只邪恶的蜘蛛,悄无声息地向这个人爬过去,一会触摸到他的喉结,一会触摸到她的乳房,一会碰到他的几吧(还有睾丸),一会摩挲她的外阴(把我一只长满黑毛的尖锐的爪子伸进阴道)。
其间,这个人问过我时间,我看了下我的手机,说了具体的时间。过后我突然醒悟过来,觉得声音可以帮助我判断这个人的性别。可是已经晚了,声音已经消失。我努力回想,可这消失的音符也像普洛司特一样,一会具有雄性的特征,一会又具有雌性的特征,弄的我精疲力竭。这些两性交织的声音在我的周围弥漫,若有若无,时强时弱,吸引我,折磨我,我的耳朵里灌满了青铜的嗡嗡声和大理石洁白的月光。
我想不起来我也可以说话,和这个人说话。这个人是肯定不会再和我说话了,撇开性别不谈,这个人显得忧伤而满不在乎。像一根发黑的沉重的羽毛,在夜晚疾行的列车上轻轻浮起。
在镇江,这个人下车,我看着这个人经过我,下车。在那一刻,我还纠缠于这个人的性别,直到背影也看不到。
我又产生了一个幻觉,觉得这个人下车时,一把把我也拽下了车。
我挣扎不脱,问:你要干什么?
这个人回答我:结婚。
然后火车开走了。
这个人拉着我一直不要命的跑着。
镇江对于我来说,完全是个陌生地方,我只在车停靠在镇江站的时候,从窗口看到过车站的一些场景。于是,这些场景在我奔跑的时候不断重复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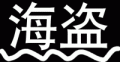 ┩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