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单相思
◎ 司屠
当时,初三(1)班有个女的叫张美丽,除了我,(1)班的男生好像都摸过她胸脯。不仅(1)班,(2)班的男同学也经常来摸。我就亲眼目睹河马、李强摸过。其时,张美丽在他们两个的挟持之下笑容可掬,左躲右避,但并不坚决,因而更像是迎合。这使得我蠢蠢欲动,很想过去摸上一把。张美丽肯定不会拒绝我,这我有把握;何况李强又向我支来了一个邀请的眼神。我的手提了上来,但随即当我清醒地意识到我在干什么时,我顺势把手放到头发上挠了一挠。之后,在东张西望了一番之后,我带着无疑是傻乎乎的微笑观望着河马他们。那里灯光昏黄,人影纠缠、摇曳,投射在女寝室的外墙上,零乱一如我徘徊斗争的内心状况。在同学们的描述中:它很大,柔软有如棉絮,而又富于弹性……我其实无非是想证实同学们的这些说法,才想摸一摸。但是,蒋静波知道了会这么想吗?这事很难保证不被蒋静波知道,张美丽一向口无遮拦;河马、李强两个又都是大嘴巴;还有其他同学,不时有同学从夜自修的教室里跑出来。我犹豫着。
话说回来,我和李强、河马的关系不比其他同学,他们肯定会为我保密的;而张美丽对于被摸早已是波澜不惊,不一定就会张扬出去;那么,我只要防备着点其他同学就是了。我悄悄地走过去,暗中出手,出手飞快(哪怕是手指在其上一掠而过也好呀),即便被同学们看到日后也有辩解的余地;或许,哈,混乱导致,张美丽以为是河马、李强摸的也说不定。不过,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谨慎起见,我还是得给自己先留好退路。然而,所谓越描越黑,到时我的辩解会不会反而暴露了我的虚弱?如果我不置一词,我能期望蒋静波会如我那良苦用心所指向的对那些谣言嗤之以鼻,而不是将它当成了一种默认吗?
犹豫再三,我终于还是没有出手。也不是没有收获了,我为自己思维之周到而不无欣慰。
我之所以不摸,是因为蒋静波。
我喜欢蒋静波。我可不想在蒋静波心目中留下“想不到蒋超也是这样的”印象。我不仅不摸,干脆掉头就走,似乎连看的兴趣也无。我也不想被蒋静波或是和她要好的女同学撞见,使她们觉得此事与我有关,我也参与了此事。与之同理,平时,每当有同学在教室里当众摸张美丽时,我始终正襟危坐,不动声色。绝非是为了要向蒋静波表明:为了你,我心甘情愿放弃了享受与张美丽相关的一切乐趣(我没有这么卑鄙)——我会偷偷地对她瞧上一两眼。我最多只能看到她的侧面,如果蒋静波不回头的话。因为蒋静波就坐在我前面旁边的位置,即赵解放的正前方,赵解放和我同桌。
蒋静波从未回头,即便平常,也很少回头,回头常常是在赵解放捉弄她时。这倒并非坏事。它使我可以随时大胆地把目光搁在她的头发包括一侧的耳廓上。蒋静波的头发乌黑,耳廓玲珑。时常,我托着腮帮,凝视良久,终于发呆。在发呆之前,我察觉到蒋静波会不时偏过头去,把左手伸入右耳边的头发,短促地理上那么一下。这可能是她的一个习惯,久已养成。而我更愿意这么认为,蒋静波是因为我的注视才养成了这一不乏生动、惹人爱惜的小小习惯。
那么,我喜欢上蒋静波,也可能是因为蒋静波坐在我前面,我老是看着蒋静波的头发包括一侧的耳廓。呵。
如今已经想不起来当时怎么会喜欢上蒋静波的。反正,在我分到初三(1)班后不久,我就发觉我喜欢上了蒋静波。这大概是一下子发生的吧。
喜欢上了是这样:我希望经常见到蒋静波。希望一早起来,蒋静波就被我发现在操场上;希望洗漱、做操时她在我旁边;希望淘米、蒸饭时和她在一起;希望上厕所会碰到她;希望课一直上下去;希望缩短午休,延长夜自修;希望星期六蒋静波不回家;希望星期六、星期日学校不放假,每天都上课;等等。
若不能见到,便念念不忘,魂牵梦萦简直。几乎每个星期日下午,我在教室里盼着蒋静波自家中返回,因之焦躁不安,突然打上一个软弱无力的呵欠或是伸一个半途便已夭折的懒腰;不时将目光投往操场、操场对过蒋静波的寝室、一旁的女厕所(需要把身体向后一仰才能看到)、学校的大门口,目光所及,无一遗漏;常常,一而再地去往大门口等候,久等不来,而又欲罢不能。此外,老是觉得听到了蒋静波的声音,看到了蒋静波的身影——竖耳再听,惟有雨声,抬头去看,空无一人,或许有人,那也不是蒋静波。此类幻觉如此真切,使人不由自嘴角绽露一抹微笑。那年九月多雨,之后,我便让目光一直地留在了窗外如注的雨水中,直至自发呆中脱身,继续重复上述过程。
又比如,上夜自修时,有人叫走了蒋静波。那天晚上,我就再也没有看到蒋静波。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似乎也只有我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一出走。我浮想联翩,不能自己。夜里一觉醒来,还是黑夜,想到此事,但愿即刻是明天。仿佛在与你的迫切作对,天却迟迟不亮,想起古人有诗“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顿时感到一阵凉意袭来,不由得抖了一抖。
总算新的一天又出现,我能看到蒋静波时——这里有这么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其他同学在场,主要是在课堂上(蒋静波就坐在我前面,这是我俩相处最为常见的方式),我感到泰然,尽管自背后欣赏着蒋静波便是;我也感到踏实,以至忘我,沉浸在学习之中。而每当赵解放一而再地拉扯蒋静波的头发,我便旁观,不乏乐趣。此时,蒋静波会转过身来,呵斥赵解放(蒋静波生气时虎着脸的样子也很好看)。但赵解放是个无赖,蒋静波越是反感,他越来劲。蒋静波后来就不再回头,只是猛然晃动身子或是用手向后打一下。如果拉扯的是我,估计蒋静波也会以为是赵解放。但我是那么老实,又怎会对蒋静波做出这种事情?确实我从未干过。
蒋静波,蒋超在拉你头发。赵解放有一次嫁祸于我。
赵解放,你不要乱说。
蒋超,你拉了还不承认,你想让我吃冤枉帐,蒋静波,这次真的不是我拉的,是蒋超。
我没有拉。我说,不免脸红耳赤。
我们争执不已,蒋静波连头也不曾回一下。这时,蒋静波的同桌也是蒋静波的好朋友方波浓开口了。似乎正是我所盼望,以及她话的内容。
蒋超,你没拉你脸红干什么呀。方波浓笑着说。
我脸红了吗,方波浓,是你的眼睛红。
呵呵呵。
我发觉在方波浓面前(在其他女同学面前也一样,前提是蒋静波就在一旁),尤其是在方波浓面前,我可谓巧舌如簧,不无卖弄。卖弄是针对蒋静波。当我和方波浓你一言我一语有如在打情骂俏时,我其实一直留意着蒋静波,我的那些话、我的所作所为不无说给蒋静波听、做给蒋静波看的意思。只是,蒋静波对我总是一副冷若冰霜模样。相反,方波浓经常回头问这问那,有事无事找我说话;每当我正确地解决掉其他同学无能为力的题目,自黑板前转过身来,目光顺势扫向蒋静波时(在踌躇满志之外,我还微露羞涩的表情,那就如同渴求着赞赏的孩子),与我四目相交的也总是方波浓。其时,我恍惚觉得方波浓就要站起来,噼哩啪啦地给我鼓上个掌。我不免有些担心,低了头,赶紧向台下走去。显然,由于我是这一届学生里成绩最好的(上届我在应届生里也是最好的,校方便把本属于我的地区三好生名额给了李强,以为李强加上15分后,我们学校就能考上两个应届生了,无奈最后吃了个鸭蛋,当时如果把15分给了我,我是能考上的),方波浓对我是钦佩有加。不仅钦佩。星期日返校时,方波浓经常会给我带来一些时鲜的零食:老菱、月饼、香蕉、柿子之类。一旦被其他男生责问,方波浓便双手叉腰,有如“豆腐西施”圆规般地站着,气势汹汹地责问他们:老娘我喜欢蒋超,怎么了,管你们屁事,嫉妒啊?
有别于第一种情况,在我和蒋静波单独相处或是直接面对(比如狭路相逢)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次,课间休息时教室里只剩下了我和蒋静波两个。幸亏我坐在蒋静波后面,但仍然不敢看她。我侧头看着窗外。一帮同学在积雪的操场上追逐喊叫,一只篮球在空中起起落落,就是不进篮框。我用眼角余光窥视着蒋静波。蒋静波埋头桌面,手中的笔在纸上簌簌作响。接下来,我大概是看着篮球出了一会神,等我不自觉地转过头来时,发现蒋静波正侧头看着窗外,拿着笔的那只手托着下巴。“嗡”的一声,我慌忙掉过头去。我也看着窗外,然而眼前朦胧,惟有蒋静波的侧面若隐若现。有如被孙悟空的定身法给定住了,我一动也动不了,感觉到朝着蒋静波这一边的脸慢慢地热了起来,越来越热,肯定已经红得一塌糊涂了。我似乎但愿这一刻尽快过去,又不乏甜蜜:由于我们一起面朝着窗外这一事实,仿佛在我们之间正形成一种默契——因而当同学们吵闹着进来时,觉得太过短暂。
事后我经常回味这一情景,反来复去,不知疲倦。并且设想,如果当时闭上眼睛任由嘴巴说出对蒋静波的喜欢,不知道后果会是如何?后果有三:一、蒋静波根本就不喜欢我;二、蒋静波不表态,此事依旧悬而不决;三、蒋静波幽幽地告诉我她也喜欢我。在我一而再地设想时,我也不是没有想到过第三种可能。仿佛可以作为印证,想起一天下午,蒋静波和方波浓窃窃私语,过了一会,蒋静波含笑推了方波浓一把,方波浓则是一贯地呵呵大笑。我故意嘟哝了一句,她们这么开心。引起了赵解放的注意,赵解放便问方波浓什么事情笑得这么三八。方波浓说,蒋静波说我喜欢蒋超,我是喜欢蒋超,蒋超,噢。我笑笑说,我不喜欢你。蒋静波看着方波浓说,人家又不喜欢你,你还,你真是……方波浓打断蒋静波,对我说,蒋静波也喜欢你。我飞快地瞄了蒋静波一眼。蒋静波显然是生气了,蒋静波骂方波浓:你神经病啊,谁喜欢——而后别过头去,在接下来长达两节课的时间里,再不理睬方波浓,直到上夜自修,蒋静波也还是爱理不理。
事过境迁,设想而已,但即使下次又有了这么好的机会,肯定我还是说不出口。不过,就是这样设想设想、回味回味,也是别有一番趣味在其中的。
类似的情形还有,当后来我们几个历届生围坐在河马叔叔宿舍里,桌上是满满摊开的书本和纸,似乎要用功一番,实际上,大部分时间是在大谈特谈与学习无关的话题,有时就会谈到蒋静波;此时,我停住笔在手指间的转动,侧耳倾听;一次,灵机一动,从此我便尽其可能地把话题引向蒋静波;每有如愿,不免窃喜,之后听得心花怒放,但愿永无止境;而当谈话往别的方向发展或陷入习惯性的冷场时,努力将之扭转、续上。我陶醉于我那手段的巧妙以及与之配套的若即若离的态度,也难免得意忘形——有时是出于对暧昧的把玩——说出露骨的语言。一旦被李强他们轧到了苗头,便再三逼问。这倒不难应付。我既不说我喜欢,也不说我不喜欢,我恰如其分地把握着这之间的度,半真半假地将此化解了。无疑,在旁敲侧击以及遮遮掩掩之中,同样包含着那种使人流连忘返的趣味。
去河马叔叔的宿舍复习是由于我们被赶出了教室。新学期开学还不到两个星期,教委出台了硬性规定,禁止历届生再在学校里复读,否则一律取消中考资格。我们一共五个,一番商议之后,一致认为离中考不过五个月时间,必须坚持留在学校附近。正好,河马叔叔在乡政府有一间单身宿舍,河马就住在那里。我们便将此当作了课堂,白天复习,吃中、晚饭时回去学校,晚上继续宿在原来的寝室里。
自那以后,我就很少看到蒋静波了。以前总能在课堂上见到,现在除了心血来潮时刻意候她外(这种时候毕竟少之又少),相逢总是偶然,理应倍加珍惜,然而,事到临头,不由自主,一如既往,我要么赶紧缩作一团,埋头自她身旁走过,仿佛没有看到;要么,向她投去百感交集的一瞥,我发觉,蒋静波目不斜视,顾自行走,仿佛也没有看到我。
方波浓我还是经常看到,方波浓会主动来乡政府找我,给我带来吃的或是向我讨教功课。其时,我把东西随便往桌上一丢,任由河马他们将它瓜分一空。有时,带来的水果数量不多,如果不是方波浓身上还留有一二,我就没份了。这帮坏蛋。吃了东西,解了题目,我叫方波浓可以走了,方波浓虽不无留恋,还是乖乖地出门去了。方波浓对我可谓是言听计从。河马他们问我有没有摸过方波浓的胸脯,和方波浓亲过嘴。我告诉他们我不喜欢方波浓,言下之意若我喜欢随时可以想亲就亲、想摸就摸。他们不理解,都觉得方波浓家里有钱,奶子看上去也挺大的,我没有理由不喜欢,况且,不摸白不摸啊。我觉得这帮家伙太庸俗了。我蒋超怎么可能因为一个女的家里有钱、奶子大就喜欢上她呢,这简直是侮辱。我只喜欢蒋静波。当我得知蒋静波家里发生了一个不幸的事后,我更加坚定了对蒋静波的喜欢。下次偶遇时,我便在投向她的一瞥中加入了怜惜。
蒋静波家里的情况是李强说知,他和蒋静波一个村。因而,在我和李强单独时,我会经常勾引他说起蒋静波。不过,虽说有时我是很想和人说说我喜欢蒋静波,我也从没对李强吐露过,更不要说其他同学了。后来有一次,夜自修期间,李强在寝室里“推牌九”赢了不少钱,便叫上我们,去乡政府旁的饭店嘬上一顿。我不会喝酒,李强非要我也喝一点。喝了酒后,我再也忍不住,我告诉他们:我,蒋超,喜欢蒋静波。恰巧,与之同时,李强和河马大声划起拳来,他们就没有听到,我说了等于没说。
在河马叔叔宿舍里复习无非一时新鲜,留在那里的时间很快越来越少。“倒春寒”那几天,早上我们睡起了懒觉;来到春光明媚的三月,中饭后我们经常上山游玩。方波浓跟着也去过一次。照顾方波浓的任务非我莫属,我颇有些不情愿地接了手。要是方波浓换成蒋静波该多好啊!于是我拉起蒋静波的手,我们手牵着手,把手甩得有如秋千荡。仿佛无意,目光一碰,随即平行。时常,我们走在队伍的最后面;会意之下突然一起发足狂奔,手或牵或不牵,若不牵,各分一头,自两边包抄,会合后再把手牵上。然后,缓慢了脚步,恢复原状,就仿佛没有奔跑过,不过,有那么一会,手是荡得更加得意了。接下来,大家组成方阵,拉手前进,大声歌唱。待进入幽暗的密林,歌声自觉低伏了下来,以至于悄无声息。队伍就此散开,蒋静波又和我走在了一起。之后一路,有光斑在莽丛间跳跃,自蒋静波的衣服和脖颈上滑过。我不时伸手去捉,蒋静波不时侧过头来嫣然一笑。后来,看得见山头的光亮,天空形成、扩大,一朵白云静止于其上,李强他们纷纷加快了脚步。我们并不着急,任由他们登上山顶,兴奋叫喊。
快接近山头时,我一步跨了上去,然后抓住蒋静波伸过来的手,把她拉到我身边。
我们并排站立。四野开阔,群山绵延,绿色的梯田层叠伸展,一堆低矮的房屋黄墙黑瓦。清风拂过,树木起伏,有如波涌。在一旁的树枝上,两只鸟儿放声啁啾,使我俩相视一笑。
(你们俩什么时候好上的,我们怎么一点也不知道?李强问我和蒋静波,河马他们也看着我们,这一问题估计他们已经憋了一路。
什么,你们在说什么,嗯,啊。
我们故作高深,语无伦次,摇头晃脑。)
随后,大家以眼花缭乱的速度下往另一面的树林。途中,蒋静波尖叫连连,气喘吁吁。蒋静波是多么的生动活泼,仿佛完全变了个人。
蒋超,你待我真好。在因奔跑而起的风中方波浓大声对我说。
什么?
没有等方波浓说出第二遍,我松开她的手,“呀——”地叫着,顾自跑远了。
每次上山,我们都走得很深,要爬上好几个山头,不觉太阳西沉,我们你追我赶,匆匆往山下赶去。山风夹带着雾,吹在身上,感到了几分凉意。往往,等我们赶到学校,李强他们的饭盒已经凉透,也有可能空了,被人偷吃了。我的饭盒之所以从未有过如此遭遇,是因为方波浓替我保管着。每当方波浓及时地把饭盒递到我手上时,它还总是热烘烘的。
然而有一次,我突然忖到,要是此事传到蒋静波那里,她会怎么想呢?她还以为方波浓已经成了我的女朋友,此事经过了我的默许。想到方波浓私下里可能常常在对蒋静波夸张着我们的交往,我狠不得立即拉了方波浓,跑到蒋静波那里,让她把我们的关系给说清楚了。
我越忖越急。
方波浓,以后你不要再拿我的饭盒了,你烦不烦你,我又不喜欢你,你脸皮怎么这么厚……我当着李强他们的面狠狠骂了方波浓一顿。
那我再把它放回去吧。等我骂完,方波浓从我手中抽走饭盒,去了食堂。
自那以后,方波浓就没有再拿过我的饭盒。不过,即便我同意她保管,也没这个机会了。很快我们就不再上山。有传言说上面要对历届生在学校周边复读情况作突击检查,我们听从好心的老师劝告,离开学校(偶尔才回),打起了游击。我们带着复习资料轮游去了各家一趟,在每个同学家中宿上几宿。名为复习,玩是必然。
李强家是第四站。去李强家的前一天晚上,就是李强赢了钱、我喝醉酒的那晚。此时,离蒋静波她们毕业剩下时间已经不多。
李强家在深坑,到了深坑,路过一屋,李强告诉我们这就是(1)班蒋静波家。我掉头去看,一个黑乎乎的门洞。我仿佛看到鲜艳的蒋静波正自其间进出。我频频回头。只是,那天是星期三,蒋静波不在。
星期六早上,河马他们在宿了三宿之后,回去了各自家。我留了下来,我有我的打算。无奈,当天下午,我数次装作途经蒋静波家,却一次也没有遇见蒋静波。难道正好这个星期蒋静波没有回家,要么蒋静波还在路上,也或许蒋静波早就到家、呆在家里没有出来。若我一个人进去她家探问,未免唐突,叫上李强那就顺理成章了。但直到晚饭吃过,我仍然不曾对李强说出口。应该说晚饭后是最好的时机了,可是,眼看上床时间逐渐逼近,我虽忧心如焚,终于还是任由时间流逝将我直接赶上了床。
第二天早上起来后,我独自出门瞎走。我确实瞎走,然而走着走着,发现眼前赫然正是蒋静波家的门洞。我慌忙向后一缩,正好路边有棵小树,我便把自己隐蔽在了它后面。蒋静波家的门开着。我痴痴地看了一会。突然,我迈出了脚步。看我的架势,仿佛我会走进屋子里去。事实是,我从蒋静波家门口走过,往前面不远处的溪坑走去了。
我听到溪水潺潺的声音,这是春天早晨的溪水独有的声音,在这之外,还有一种好像是棒槌敲打衣服的有节奏的声音。接下来,估计我会沿着溪边走上一会,或者下去洗把手,无非如此。但就在这时,我看到了蒋静波。确有人在洗衣服,那人是蒋静波无疑,虽然她背对着我。我顿时止住脚步,心跳怦怦,呼之欲出。蒋静波就在我身下不过半米的地方,我只须向前走上两、三步,就能下到她身边。我向前踅了半步。蒋静波似乎注意到了身后有人,回过头来,回得并不充分,应已看到我。仿佛没有看到,蒋静波迅即转过头去,手中的棒槌落在了衣服上。蒋静波“砰砰”又敲了两下,而后停下,改为搓洗。
我居高临下,感到有一种优势,但很快被阵阵烦躁取代。急中生智,我说出一句话来。
蒋静波,我们五百年前是一家,我也姓蒋。
这是我认识蒋静波以来对她说出的惟一一句话。
我搔了搔头。
蒋静波停止了手上的动作,看着水面。我也看着水面。我们一起看着水面。
过了一会,我轻轻的——轻得大概只有我能听到,如同在喃喃自语——说:我走了。我就离开了蒋静波身后,在溪边迂回了一阵,回去了李强家。一路上,我感到内心荡漾,无以名状。我把外套解开,让春风扑面吹着,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好,我轻快而又不无羞涩地哼起了一支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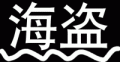 ┩目录┡ |